清晨四时许,梁肇怀的钥匙串在车间铁门上撞出轻响。他总比规定时间早来半小时,不是为了表现,是怕自己手脚慢。这个从文学院走出来的“书生”,花了三年才让自己的动作赶上老酿酒工的节奏。

回想起刚进茅台的时候,梁肇怀总觉得自己像个笨拙的学徒。第一次学上甑时,他总把糟醅撒成“小山包”,蒸汽冒得不均匀,老师父急了:“你这是酿酒还是堆雪人?”他不吭声,回到家就对着镜子比划“轻撒”的手势,手腕酸得抬不起来,就用热毛巾敷着继续练。同事们笑他“读书读傻了”,他却在笔记本上写:“上甑如写字,一笔一划稳当,才有模样。”
2012年,梁肇怀获评“安全生产月优秀个人”,他上台领奖时紧张得直搓手。那时候他已能闭着眼摸出糟醅的发酵情况和水分含量,靠的是每天下班前抓十把糟醅捏揉,把触感记进肌肉里。“我没别人聪明,就得多下笨功夫。”他摩挲着笔记本里夹着的老茧照片,那是2015年磨破手掌时拍的,“疼得握不住笔,但想着再练半个月,说不定就顺手了。”
随着经验积累,梁肇怀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。在他的笔记本里,2017年的记录格外密集。那年他当班长,班组来了批新粮,他总觉得糟醅发酵得不好,于是每天测三次温度,画了整整一本曲线图。“别人说我太轴,粮食每年都不一样,测这么细干嘛?”他指着其中一张折线图,“你看,发酵速度慢,数据不会骗人。”
当酒师后,梁肇怀依然保持着“笨习惯”。每轮次每个糟堆发酵都要取好几次糟醅样本,放在手掌里细心观察,放在鼻子旁边嗅,用手指反复碾。“有次徒弟笑我像在做化学实验,我说对,咱们做的就是‘粮食的化学’。”

梁肇怀(左)传授徒弟朱书刚(右)堆积发酵知识
对于带徒弟,梁肇怀有着自己的坚持。徒弟朱书刚至今记得,自己初任副班长时急于展现能力,提出想研究一套摘酒的机器设备,被梁肇怀拦住了:“改工艺不是换衣服,得知道哪里不合适,才能缝补。别急着变,先把老法子吃透,亲自摘酒你才能感受到第一滴茅台基酒流出的温度。”朱书刚现在也学会了这股子“慢劲儿”,带领上甑员工时总爱叮嘱,“先看会,再干会,最后想会。”
在班组,梁肇怀不仅对年轻员工悉心指导,对老员工的困惑也从不吝啬帮助。班组员工熬杰在晾堂干了十几年,去年转岗学上甑时总抓不住“轻松薄匀平准”的要领。“我看别人撒糟醅像撒雪花,自己一上手就成团。”熬杰不好意思地挠头,“梁师没嫌我笨,专门挑了个空甑桶给我‘开小灶’。”

梁肇怀(右)向熬杰(左)示范上甑要领
“你瞧,手腕要突然使出一个顿挫力,糟醅才能散开飘出去,就跟下小雨似的。” 梁肇怀撸起袖子,亲自演示,手腕翻转间,浅褐色的颗粒均匀铺在甑篦上,蒸汽透过缝隙稳稳升起。他让熬杰跟着做,自己蹲在旁边用手机拍下视频,一帧帧慢放讲解:“你看这儿,手腕僵住了,糟醅就堆在一起,蒸汽顶不上来,酒就出得慢。”
这样的一对一教学,梁肇怀从未间断过,当熬杰终于上出令他点头认可的“雪花甑”时,那份欣喜溢于言表。“那天他比我还高兴,现在我上甑,同事们都说我‘有梁师的影子’。”熬杰摸着甑桶边缘的围边感慨道。
班组墙上的“荣誉树”下,摆着梁肇怀的第一本工作笔记,扉页写着:“师父说我手笨,但心不笨。”这是2011年师父给他的评语。如今他带徒弟,最常说的话是:“酿酒就像挑水,桶里的水晃不晃,全看你步子稳不稳。”2023年班组拿了车间第一,他红着脸说:“我这人不会说漂亮话,就觉得将每把糟醅翻匀、每个温度记准,比啥都强。”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车间,梁肇怀又蹲在窖池边发呆。他常盯着糟醅里看不见的微生物出神,想着这些“酿酒师”到底怎么把粮食变成美酒。

有次徒弟问他:“师父,你说我们酿的是酒,还是时间?”他想了半天回答道:“是把笨功夫酿成了巧劲儿。”排间休息时,他习惯到生产房旁边的小花园里面待一会儿。看着远处的赤水河波光粼粼,他想起母亲做的豆瓣酱——同样是把豆子、盐、阳光拌在一起,时间到了,自然出香味。“酿酒和过日子一样,急不得。”他摸出帆布本,记下今天的感悟:“好手艺不在手上,在心里——心里有谱,手才稳当。”
一审:李姿 何雪沙
二审:陈杨 蔡忠成 方存芳
三审:王幸韬 吴德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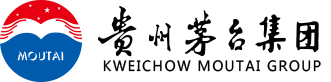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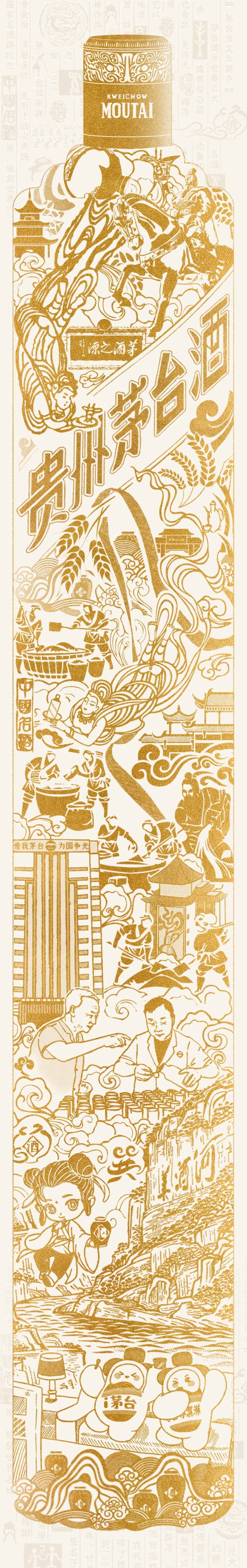







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抖音号
抖音号 巽风
巽风 下载 i 茅台
下载 i 茅台